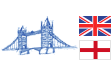英国伦敦留学社区
London Chinese
对雕塑家张得蒂的访谈
haoyi007(2013/11/5 16:57:12) 点击:265055 回复:0 IP:110.* * *
haoyi007(2013/11/5 16:57:12) 点击:265055 回复:0 IP:110.* * *
对雕塑家张得蒂的访谈
初见雕塑家张得蒂,便诧异于她那矍铄的精神和敏捷的行动,令人难以相信她竟然年至耄耋。与张得蒂老师对话下来,更感慨于她在最宝贵的人生阶段所经历的苦难折磨,竟丝毫未磨损正直的品质、奋发的精神,却又多一分风雨历练出来的淡定从容。怀抱着对艺术坚定的单纯的热爱,她雕塑着,雕塑着,雕塑着……
“没办法,赶上了那个时代!”
笔者:张老师您好,从您的人生经历中,我觉得您身上有很感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!你认为呢?
张得蒂:我哪有这么好啊,只是没办法,赶上那个时代了。
我爸爸是20世纪初最早赴美国的留学生之一。可他回国就赶上军阀混战,没有办法实践他自己的理想。他们那个年代,知识分子特别痛苦。我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(40多岁)就死了,那时我才11岁。我娘是宋庆龄的学生,也是山东省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。我娘觉得妇女就该解放,女子必须要有本事有职业才能救国,才能真正地解放。为了事业,他们要孩子也要得晚,生我的时候我母亲都30多了,我父亲快40了。我母亲认为,既然当母亲就不能再工作了,就当一个好母亲,她就辞去了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的职务。她在山东的时候很受人尊敬。大家都叫她朱老师,好像没有名字也没有辈分。我就生活在这么
个家中。
笔者:相信母亲一定对您有非常深刻的影响。您是怎么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呢?
张得蒂:从我5岁开始,中国先是军阀混战,再是抗日战争,后来又是解放战争,经历的都是不太平的时代。我家住在济南,那时候我家所在的那个院子解放战争时就是枪毙人的地方。战争期间,我和同学、家人颠沛流离,到处逃难。我才十几岁就经历了很多次生死灾难,所以对很多事情也就不怎么害怕了。
笔者:那么个动乱的时代,确实很无奈。让我好奇的是,您父母都不是从事艺术的,您怎么会走上艺术的道路?
张得蒂:我爸爸说了,孩子当中一定要有人学矿。我弟弟认为我不适合学数理化,不让我学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,见个人就说我给你画个像。我父亲喜欢画画喜欢书法。他思肺结核在家时就给我一本一本地画小人、画动物,算是对我的美术启蒙。我有一个姨在北京。她建议我考美院,我就去考,没想到就考上了。我的爱人张润垲也参加了考试,还考了第八名。结缘雕塑
笔者:您怎么会选择雕塑这个专业呢?
张得蒂:当时各个系老师来到预科班竞选,滑田友和邹佩珠先生来动员大家选雕塑专业,说学雕塑不是为了个人成为艺术家,而是集体来搞纪念碑。我们当时就觉得除了学画画原来还有这么伟大的事业。我的身体好,也不怕吃苦,就报了雕塑系。
后来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,社会上没有要搞雕塑的人也没有人需要雕塑。学校就说,你们留下当研究生吧,让3个年轻的老师带着你们,要是有了任务你们干点活挣点钱,自己奋斗着做一个工作室。就这么着当研究生,正好赶上建北京展览馆(原名苏联展览馆),建筑上面的装饰雕塑及里面柱子上的小动物都是我们做的。还有王府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展览馆正门上方的浮雕,也是那时候老师带着做的。我们1955年秋天就毕业了。毕业后把我分去创作辽沈战役纪念碑,还没做完就被打成右派了。
笔者:我了解到您被下放到北京、河北农村的3处地方,加起来差不多10年。这期间是否有机会从事雕塑创作?
张得蒂:有,中央美院复制收租院的时候就把我调回来了。我在雕塑系学习时还挺用功的,也算能吃苦。后来,我参与《农奴愤》雕塑创作,1974、75年的时候在西藏。挺感激那个时期我们创作组对我的照顾。他们没有告诉西藏人民我是右派。藏民对我特别好,家长也很愿意让小孩跟我一块玩。有个叫达娃的6岁小孩和我关系很好,一听说我要走了他就亲我的手。后来回北京,我脑子里老想着这个小孩,就做了一尊藏族小孩的塑像《小达娃》。还有参与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的创作。建毛主席纪念堂时,全国调来了90多位雕塑家,就我一个人是右派。当时在那整天提心吊胆、战战兢兢。有学生去参观我们做雕塑,就说我,你怎么看起来脸色苍白,要休克了,其实是害怕。这种恐惧也导致我突然进入更年期,当时我才45岁。“真的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了!”
笔者:做《小达娃》的时候是1978年,这时您已经47岁了。一般对女性而言,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,是什么促使您坚持走雕塑创作的道路呢?
张得蒂:当时很多因文革被平反的人,社会上提出“要把失去的10年时间抢夺回来,被平反的右派们是想把失去的20年时间夺回来。但当年我47岁,还有8年就要退休了,还干不干呢?心里特别矛盾。当时看到一句名言“只要有决心,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”。张润垲说:“你心里除了雕塑什么都没有,不干你没法活下去。你努力干,我帮助你。”这样他一帮就是30年。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,真的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了。
笔者:那么您是怎么开始“夺”的?
张得蒂:我在农村劳动的时候,不让画,也不让做雕塑,我就想着雕塑,偷着在本上画,有件小孩弹琴的雕塑就是那时候偷着画下来的。我就想头怎么做,手怎么做,一天的劳动就不那么痛苦了。好多作品都是在劳动时想出来的。平反以后,我想我当不了大雕塑家,我就做点作品给孩子们补点人性吧,这样我也没有白活。你们孩子们不知道批判人性论有多可怕。没有家庭,没有友情,没有亲情,没有笑声,什么都没有了,人和人就是阶级关系。当不了大雕塑家,我之前总觉得特别遗憾,到了70多岁以后才想通,一个雕塑家不一定都要做大主题的作品。
笔者:可以说那段下放劳动的日子,从另一个角度讲可能让您更贴近真实的生活,体验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,为您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。
张得蒂:这是一方面,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情感上的体验,特别朴素、特别真诚的情感。
笔者:我看到您从1978年开始,除了创作批唯美温情的作品,还做了很多纪念性肖像雕塑。
张得蒂:一开始做体现人性的作品,我没想到社会这么需要。后来慢慢地,人们的心态开始平复了,我觉得我的历史责任吧,得为我最尊敬的人被迫害的人做一批速写头像,心里有种迫切抢时间的感觉。
那时候电话很少有,我每打听到一个地址,就骑上破自行车,车前面放一大筐泥,后面是脸盆啊石膏啊架子啊,直接就上人家里去做了。我的家人担心这么唐突地过去,人家会不会不高兴。但是他们都特别友好。艾青说,我最不爱给人当模特。我抱着泥就着急了,大声问,那我呢?艾青说,好好,给你当给你当,你说要做几天都行。我的创作速度越来越快,一开始做彦涵、艾青先生的塑像,四五天才能做完,后来有的塑像一天就做完了。我想,把活着人的精神面貌“抢”下来,找到体积感就行了,不要太细致。早上敲门和人商量好了就赶快做,一直做到晚上,我用石膏把它糊上,因为怕碰了就自己拖回来,这么着一整天很快过去了。
本篇文学艺术论文转自194论文网,具体地址为:
http://www.194lunwen.com/html/yishu/yishulunwen/2013105236.html
初见雕塑家张得蒂,便诧异于她那矍铄的精神和敏捷的行动,令人难以相信她竟然年至耄耋。与张得蒂老师对话下来,更感慨于她在最宝贵的人生阶段所经历的苦难折磨,竟丝毫未磨损正直的品质、奋发的精神,却又多一分风雨历练出来的淡定从容。怀抱着对艺术坚定的单纯的热爱,她雕塑着,雕塑着,雕塑着……
“没办法,赶上了那个时代!”
笔者:张老师您好,从您的人生经历中,我觉得您身上有很感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!你认为呢?
张得蒂:我哪有这么好啊,只是没办法,赶上那个时代了。
我爸爸是20世纪初最早赴美国的留学生之一。可他回国就赶上军阀混战,没有办法实践他自己的理想。他们那个年代,知识分子特别痛苦。我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(40多岁)就死了,那时我才11岁。我娘是宋庆龄的学生,也是山东省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。我娘觉得妇女就该解放,女子必须要有本事有职业才能救国,才能真正地解放。为了事业,他们要孩子也要得晚,生我的时候我母亲都30多了,我父亲快40了。我母亲认为,既然当母亲就不能再工作了,就当一个好母亲,她就辞去了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的职务。她在山东的时候很受人尊敬。大家都叫她朱老师,好像没有名字也没有辈分。我就生活在这么
个家中。
笔者:相信母亲一定对您有非常深刻的影响。您是怎么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呢?
张得蒂:从我5岁开始,中国先是军阀混战,再是抗日战争,后来又是解放战争,经历的都是不太平的时代。我家住在济南,那时候我家所在的那个院子解放战争时就是枪毙人的地方。战争期间,我和同学、家人颠沛流离,到处逃难。我才十几岁就经历了很多次生死灾难,所以对很多事情也就不怎么害怕了。
笔者:那么个动乱的时代,确实很无奈。让我好奇的是,您父母都不是从事艺术的,您怎么会走上艺术的道路?
张得蒂:我爸爸说了,孩子当中一定要有人学矿。我弟弟认为我不适合学数理化,不让我学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,见个人就说我给你画个像。我父亲喜欢画画喜欢书法。他思肺结核在家时就给我一本一本地画小人、画动物,算是对我的美术启蒙。我有一个姨在北京。她建议我考美院,我就去考,没想到就考上了。我的爱人张润垲也参加了考试,还考了第八名。结缘雕塑
笔者:您怎么会选择雕塑这个专业呢?
张得蒂:当时各个系老师来到预科班竞选,滑田友和邹佩珠先生来动员大家选雕塑专业,说学雕塑不是为了个人成为艺术家,而是集体来搞纪念碑。我们当时就觉得除了学画画原来还有这么伟大的事业。我的身体好,也不怕吃苦,就报了雕塑系。
后来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,社会上没有要搞雕塑的人也没有人需要雕塑。学校就说,你们留下当研究生吧,让3个年轻的老师带着你们,要是有了任务你们干点活挣点钱,自己奋斗着做一个工作室。就这么着当研究生,正好赶上建北京展览馆(原名苏联展览馆),建筑上面的装饰雕塑及里面柱子上的小动物都是我们做的。还有王府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展览馆正门上方的浮雕,也是那时候老师带着做的。我们1955年秋天就毕业了。毕业后把我分去创作辽沈战役纪念碑,还没做完就被打成右派了。
笔者:我了解到您被下放到北京、河北农村的3处地方,加起来差不多10年。这期间是否有机会从事雕塑创作?
张得蒂:有,中央美院复制收租院的时候就把我调回来了。我在雕塑系学习时还挺用功的,也算能吃苦。后来,我参与《农奴愤》雕塑创作,1974、75年的时候在西藏。挺感激那个时期我们创作组对我的照顾。他们没有告诉西藏人民我是右派。藏民对我特别好,家长也很愿意让小孩跟我一块玩。有个叫达娃的6岁小孩和我关系很好,一听说我要走了他就亲我的手。后来回北京,我脑子里老想着这个小孩,就做了一尊藏族小孩的塑像《小达娃》。还有参与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的创作。建毛主席纪念堂时,全国调来了90多位雕塑家,就我一个人是右派。当时在那整天提心吊胆、战战兢兢。有学生去参观我们做雕塑,就说我,你怎么看起来脸色苍白,要休克了,其实是害怕。这种恐惧也导致我突然进入更年期,当时我才45岁。“真的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了!”
笔者:做《小达娃》的时候是1978年,这时您已经47岁了。一般对女性而言,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,是什么促使您坚持走雕塑创作的道路呢?
张得蒂:当时很多因文革被平反的人,社会上提出“要把失去的10年时间抢夺回来,被平反的右派们是想把失去的20年时间夺回来。但当年我47岁,还有8年就要退休了,还干不干呢?心里特别矛盾。当时看到一句名言“只要有决心,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”。张润垲说:“你心里除了雕塑什么都没有,不干你没法活下去。你努力干,我帮助你。”这样他一帮就是30年。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,真的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了。
笔者:那么您是怎么开始“夺”的?
张得蒂:我在农村劳动的时候,不让画,也不让做雕塑,我就想着雕塑,偷着在本上画,有件小孩弹琴的雕塑就是那时候偷着画下来的。我就想头怎么做,手怎么做,一天的劳动就不那么痛苦了。好多作品都是在劳动时想出来的。平反以后,我想我当不了大雕塑家,我就做点作品给孩子们补点人性吧,这样我也没有白活。你们孩子们不知道批判人性论有多可怕。没有家庭,没有友情,没有亲情,没有笑声,什么都没有了,人和人就是阶级关系。当不了大雕塑家,我之前总觉得特别遗憾,到了70多岁以后才想通,一个雕塑家不一定都要做大主题的作品。
笔者:可以说那段下放劳动的日子,从另一个角度讲可能让您更贴近真实的生活,体验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,为您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。
张得蒂:这是一方面,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情感上的体验,特别朴素、特别真诚的情感。
笔者:我看到您从1978年开始,除了创作批唯美温情的作品,还做了很多纪念性肖像雕塑。
张得蒂:一开始做体现人性的作品,我没想到社会这么需要。后来慢慢地,人们的心态开始平复了,我觉得我的历史责任吧,得为我最尊敬的人被迫害的人做一批速写头像,心里有种迫切抢时间的感觉。
那时候电话很少有,我每打听到一个地址,就骑上破自行车,车前面放一大筐泥,后面是脸盆啊石膏啊架子啊,直接就上人家里去做了。我的家人担心这么唐突地过去,人家会不会不高兴。但是他们都特别友好。艾青说,我最不爱给人当模特。我抱着泥就着急了,大声问,那我呢?艾青说,好好,给你当给你当,你说要做几天都行。我的创作速度越来越快,一开始做彦涵、艾青先生的塑像,四五天才能做完,后来有的塑像一天就做完了。我想,把活着人的精神面貌“抢”下来,找到体积感就行了,不要太细致。早上敲门和人商量好了就赶快做,一直做到晚上,我用石膏把它糊上,因为怕碰了就自己拖回来,这么着一整天很快过去了。
本篇文学艺术论文转自194论文网,具体地址为:
http://www.194lunwen.com/html/yishu/yishulunwen/2013105236.html